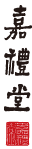盡美盡善:格義大學之道
鄧國光
澳門大學中文系
一、大學之道,是文明之路
文明的生髮,顯示人類嚮往優美、善良、平和、榮譽與幸福的集體願力。源遠流長的中國歷史,文明的核心是“禮”,涵蓋了所有足以活化個人與社群的生活形態。考察原生“禮”,都不離“樂”。為禮必須備樂,禮、樂共同組織了廣義的“文”,這是經歷三代的智慧累積,構成了文明的願力向度。《論語‧八佾》謂:“子謂《韶》,盡美矣,又盡善也。謂《武》,盡美矣,未盡善也。”對《韶》樂“盡美盡善”的讚頌,是考察的起點。
順歷史流程張開理解的世界。先看魏何晏《論語集解》引孔安國的注:“《韶》,舜樂名也。謂以聖德受禪,故曰盡善也。《武》,武王樂也。以征伐取天下,故曰未盡善也。”這是從帝舜和周武王執政的過程立論,以“聖德”論定。這是第一種說法。
其次是梁皇侃《論語義疏》,謂:“天下萬物樂舜繼堯,而舜從民受禪,是會合當時之心,故曰盡美也。揖讓而伐,於事理無惡,故曰盡善也。天下樂武王從民伐紂,是會合當時之心,故曰盡美也。而以臣伐君,於事理不善,故曰未盡善也。”這是強調周武王伐紂的“事理”為說,指出有違君臣道義,所以《武》“未盡善”。這是第二種說法。
唐孔穎達《禮記正義·樂記》則認為“未盡善者,文德猶少,未致太平”,說周武王伐紂,“文德”尚未能圓滿實現致天下太平的理想。孔穎達疏文說的“文德猶少”,是非常謹慎的解說。“太平”是“盡美盡善”的境界,文德乃體現理想政治的質性。這是第三種說法。
至唐為止,大抵流行此三種說法,於《韶》無異議。差歧在《大武》,都是在“德”義上解讀,表明美、善之間,尚存“德”的差異,不是等義。于漢、魏儒者,謂之“聖德”,于隋、唐儒者,則稱“文德”。“聖德”與“文德”意涵相同,聖是終極的理想人格,則文之通於聖,便絕非等閒事。但須注意的,是“未盡善”不能等同“不善”。
古代的解釋焦點,不離帝堯與周武王德性高下的比較,這是依據文本的內在理路的解讀。蘊含對整體幸福的集體追求。長期文化累積所構成的思維定勢,聖道形成集體的應然追求。于文獻記載《韶》樂源出帝堯,在詮釋過程中自然根據帝堯事蹟的文化沉澱加以論定。帝堯事蹟是一個確定為聖王之治的歷史時刻,詮釋過程中的集體前設認識支配了解釋的向度,透露出對整體善的集體祈盼。
二、通融“盡美盡善”與“聖德”
回到文本為中心的語境解讀,方能夠超越集體的時代焦慮所致的精神空虛,重新接通實在的德性大流,讓聖德大方地出場。從生生不息的道義潛流說“盡善”的“盡”,便是表達一精神上達的進路,而非指事情盡頭與現象的邊限。“盡善”指向圓滿無瑕的道德造境,一種從內心出發而輻射出的實踐力量,即是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的聖道實現過程,一步一步通向全體生命的圓足。
“盡善”的大前提,是肯定道德自身存在,具體實現圓滿的可能性。生命上達開出的豐足性,利己利他而獲得絕對的圓滿,是謂“圓善”。建基於全體幸福的聖德,張開全幅坦蕩的精神世界,通感天下,於是不論古今中外,皆由衷感動讚美。這便是盡之的互動精神。因帝堯之德,而由衷讚美《韶》樂;再因對《韶》樂由衷的讚美,而寄託帝堯聖王之德。《韶》樂成為為至德造境的寄寓,孔子的讚美成為一個實現道德自我圓滿的通感過程。音樂之美與道義的極致,相通不可分。推而言之,藝術與倫理,是一體的兩面,合之則美,裂之兩傷。
“盡善”與“盡美”向度一致。《武》的造境“盡美”,“盡美”指藝術美的境界。在孔子語境中,“盡美”是可取的,但只是未至登峰造極。《韶》之“盡善”,則表明更高一層的可能,德性所可實現。道德推至極處,便是通明的聖。“聖”義於今天甚隔膜,甚至在當代思想中徹底失落,只淪為冷嘲熱諷的話頭。莊子認為天地有“大美”,非人力所能為,是針對式儒家的表達策略,類似反話。反話容易說,表現機鋒,能夠聳動耳目,卻非心身安頓的方劑。追溯其針對的源頭,離不開孔子說的“盡美”。顛覆“盡美”的意義,便突出不能言說、只可意會的“大美”。但顛覆了“盡美”,字面上取了浮面的效果,並不表示“大美”為實至名歸的人生歸宿。因為,孔子所追求的,是淩駕於“盡美”的至善,“盡善”方才是極致。而孔子稱讚《韶》、《武》之樂“盡美”,“盡”義比“大”更甚。“大”屬於平面的空間觀念,是相對說的。“盡”字說的是動態的人生上達進程,從主體的精神境界說,意義是絕對的。以其中蘊含的積極樂觀精神,足以鼓舞人心,推動整體的向善。相對而言,莊子刻意的超越,其足以澡浴凡思,而不能感奮生命。生命感奮而相通,是稱之為活。
孔子儘管是天縱的大聖,亦不可能無中生有。他之所以對《韶》、《武》之樂的感覺有所差等,是基於歷史知識的認知與反思。這份知識與良知的積累,成為判斷的“理解”。舜以及周武王姬發的歷史事蹟,是對比論定的基礎。然而只有孔子透過音樂的敏銳度,察覺“美”和“善”的深層差異,從而概括這件歷史事件的本色意義。
因《韶》樂而通感“道”,體現極深刻的現實關懷。在孔子的思想世界中,堯、舜屬於“禮樂征伐自天子出”的有道的時代。有道可循的政治生態是為“王道”。殷商箕子《洪範》宣示“王道平平”,為東周的思想共調。《韶》樂出自聖王,自然體現“王道平平”的精彩,這就是“盡美盡善”。中國遠古遺留下來的《書》、《詩》,是現實生活的片斷記載,已經充分人文化。其中不存在神、人相危害的悲劇命運內容,無須回避天道或神道,更能夠顯示個體與生存世界的整體關係,而不致以自我割裂為事,最後回歸天人同和的境界。這境界融通了道德與藝術,表現於極度純粹的聲音與音樂世界。
三、“文質彬彬”與“充實之謂美”
先秦聖王觀的終極人格是表現於“聖德”,聖德與聲音之道相通。聖的本意,原指聽聲本能,演變提升為通德的道德理性,深契天人。因而於“道”的體認,必須出自內在智慧的通應共感。“盡美盡善”便是孔子默契“道”境的體驗,相應的王道教化理想,自然要求生活意義的和諧與完整,不容割裂撕碎或偏於一隅。道德的人生必然是藝術的人生,有道的社會亦是生氣勃勃的整體,其中包涵道德與藝術圓融、各體與整體的共存共榮,這都顯示充沛而活躍的生命活力,生生不已。自感應的一刻而通達六合古今,其中只有至美至善,猶如無形質可言的悠揚旋律,生命通暢,擺脫一切對立與紛擾,完美屬於絕對純粹的狀態,謂之大同的境界,是一種曾經實現在《尚書》堯、舜敘述的集體文化記憶。
孔子聞《韶》,感受到“道”的存在境界,“盡美盡善”是與“道”相契的感覺描述。這境界已超越固定的時空意義,悠然地體存了永恆的上達與奮鬥的精神。因此,孔子“在齊聞《韶》,三月不知肉味”,相對于永恆的存在體驗,在特定時空之中的本能享受,已變得毫無留戀的餘地了。
在完美而純粹的前提下,落在個體生活上,便是孔子強調的“文質彬彬”,一種理想的君子修養。從個體說,聖人不是那麼容易成就,但能夠從自身心靈開出通透無暇的道德品質,成己成德,然後推而廣之,即使未能大用而成就治國、平天下的偉業,生命依然處於上達的境地,充滿文采美。這種建立在成德基礎上的文采美,也是道德與藝術的優美配合。從自律德性發旺的意義,展示的生命色彩,則原原本本,文采美是人生不斷“充實”的歷程。
孟子說“充實之謂美”,在先秦儒家的語境之中,美之為義,不純是感覺,還是人生不斷的過程,追求“求仁得仁”的精神上達。孟子概括的良知良能,視為充實的原動力,不存任何造作和虛假。此自律德性的良知良能,所建立的文采美,原心開啟,自然澄明通透。美更上層樓,便是道德純粹的“聖德”。文采之美,皆根源人心的本然,了非虛偽造作,亦非安止於靜態之中,更重要的,是顯示非常的生命上進動力。
四、經世的進路
《禮記·大學》是先秦時期的人寫的,雖然不是孔子寫的,但能經歷種種時代的洗禮,表現從意志到現實的關係的歷程,概括了中國經學的經世之路。儒者都是由“修、齊、治、平”開展出對世界的關懷,儒家不放棄物質的追求,但堅持與眾同樂。這是以心比心,自己富有,希望別人也富有,是儒學的開放性。歷來的對儒家的批判,出於遷怒,把孔子演繹成孔乙已,這只是某一階段的文化想像。風浪過後,孔子依然如故,分毫無損。
馮友蘭先生從“修、齊、治、平”進講秦漢以來二千年的經學時代的理想向度,極正大。格義于此路開展。修,美也;齊,互敬之謂。《禮記·曲禮》頭一句便說:“禮無不敬。”治,理也。治,從水,理本字是裡,從田從土,治理即整頓“水土”。非水無以生,戰國荊門楚簡中存佚文題曰《太一生水》,謂宇宙以水為原始。這是大智慧的究竟,不得了。土者生生之所,非土無以長養,故五行以“土”為中心,土德乃王之性。平,豐也,富也。平天下,意取富天下所有民庶。修齊治平的經世目的,非常明確。
“修”是指美,孟子曰充實之謂美。20世紀80年代初李澤厚先生寫《美的歷程》,強調充實是由生氣展示出來的。後人把“修”解作臘肉,是後起的意義,用來解釋《論語》是不對的。“束修”,指整束美行、儀容端莊。如果具有這種道德自覺,孔子一定會教導。現代人說的美化,只是虛飾,在古代則是以意志充實自己。
上善若水,是老子說的。孔子曾求教過老子,二人並不矛盾。矛盾的是後人。以水作為智慧的泉源,“修”是指意志人格的影響,如水一樣,潤澤萬民。杜甫“隨風潛入夜,潤物細無聲”,就是這意義。
“齊家”是指互相尊重,一出於敬。“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”,是在生活層面說,小人是指平民,從古至今,“禮教”並未有深刻影響平民生活,平民平常身體互不接觸,是因為衛生條件。齊,敬,聲近義通。互相尊重,構成生活的和睦。盡自己的本份,而不看對方如何,世界如何變,自己都不會變。修齊治平,主張社會身份可轉移。君主勞心,民眾勞力,心力是一體的,君臣共治。五德是有終始的,君可以終可以始,不能永久把持。人君有德,才所以作民眾的中堅。周代的族內婚姻,導致互不信任,所以會把長子殺掉,或廢長子。孔子提出選賢與能,以德代位。齊家是以德齊家。中國思想中,只有儒家講性,突出德性是可以互相感染的主張。告子說的“食色性也”,沒有不妥。只是孔子、孟子強調道義自覺的能力,意義何在呢?要知道這些言論不是教訓小民百姓,而是教導人君。若瞭解當時管治階層的家庭關係,便知道這些言論在扭轉周人的野蠻落後。
“國”是指身所在的都城,現代的國是nation,是政權,古代是指土地。範圍封域,治即理。治是水旁,治水是古代之大事。大禹治水後,羅亞方舟後,出現另一個世界。在先秦年代水為世界之源,太一是最原始的世界。太一生水,表明水的重要性。鐘本字是滴,水滴的規律可以計算時間。滴水雖小,但經過時間,足以穿石。
“理”,在先秦文書中,只有裡,從田從土。田,正音讀為電,是整理土地之意。整理土地需要與水一同治理,所以,治理土地是古代經世之要事。儒家的治國,不但是指管理人的行為秩序,而更須治理水土。水土治好了,百姓豐足,才可講求禮儀與文明。
“平天下”,是指天下各安其份。平是安的意思,安的意義極大。生活種種問題,大體來自不安。對症下藥,便提出安的要求。儒家肯定人性是有參差的,上智與下愚不移,須要教導治理的是中材。因此,有了這一層對人性的瞭解,便知“平天下”是使人世間大部分屬於中材的人,能夠各盡其性,各得其所。上智是不用管的,下愚雖不能變化質性,但為政者有責任令他們生活安好。儒學是一種厚道,不會偏側一面。
牟宗三先生強調《大乘起信論》“一心開二門”的普遍意義,因為這包容的觀念,足以說明意志力對生活世界所引起的無限可能性,透露出把自己作為生活世界的主人翁。《大學》也是如此大開光明之途。
孔子提出以德代位,以修養代替血統的觀念,漢初行的是黃帝之術,由漢至唐,都是女性主導的年代,是較自由的社會。對母親較尊重,以一句父系社會概括二千年中國歷史是不妥當的。漢武帝用董仲舒,是因為母親竇太后太能幹。漢武帝的叔叔劉安寫了一本《鴻烈》,即《淮南子》。第一篇《原道》就是指治國之道,劉安希望建立一個完善的帝國,成為後世的模範。竇太后的無為而治,是容忍之治。說漢武帝獨尊儒術是誤解,竇太后死後,漢武帝不能忍,吩咐淮南王劉安前來見他。漢武帝給劉安寫好《離騷傳》後,將其全族殺掉。《鴻烈》得以流傳,因為書中有重大的價值。《淮南子》說的是五德終始。事實是漢武帝從未重用董仲舒,今天看到的《春秋繁露》,是後人重輯。儒學從未支配中國,更罕見仁義之道的實行。
禪讓或五德終始論,都是美化奪取政權的醜行,掩飾“打天下”的殘酷手段。而“治天下”是由“經”治天下的,治理是管理水土、生產資源,而不是管制百姓的私生活。歷來的經世之書,關鍵是要治河,唯有治理好水土,國勢才會蒸蒸日上。唐代開始,大運河成為帝國的核心。南宋開始,出現港口。男女社會地位的轉變亦由宋朝開始。因為男子有商業,女子可有可無,地位就越來越低。漢、唐因為是土地社會,男耕女織,所以男女較為平等。男女地位的問題,不能動不動便罵孔子。儒家從來不排斥女子。孔子、孟子是靠母親養大的,豈會鄙視女子!
五、治世的雙軌向度
中國經學離不開《春秋》,離不開華夷。華是指中國,夷是指文化程度低下的地區。經學的精神指向,“治”有兩層,一要治水土。其次是華、夷的關係。這對生活世界的保衛與開拓。稱為華、夷之辨的對外方式,與治理水土,成為經世的“治”的雙軌。單軌則變成一足的怪物,不可行的。“獨尊”儒術的說法是怪胎,必然會導致反面。
生存世界離不開農、牧。“格物”就是格農、牧。沒有空間與層次,世界不能顯示。格物則平。古無輕唇音,平天下音義同豐天下。對水土治理,必須解決擁有權的問題,沒有擁有權就人人都不理。擁有的觀念就帶出認同感,有認同感才會珍惜。治理水土背後是民族對文化的認同與愛護。屬於自己才會珍惜,是物性的特點。這些道理,孟子已經講得很透徹。
治理水土的經典經驗,來源來自《尚書·堯典》。透過公義方式,考驗舜的能力。舜是選舉出來的,不是禪讓。《尚書·禹貢》記載大禹治水,分天下為九州,天下得安。這篇古典,記載了禹的功勞。“貢”是顯示地方百姓對朝廷間恩惠的往來。治水以後,百姓生活豐足,於是把土物上貢朝廷,以示報答。這種恩深義厚的關係,稱之為“平”。在平清的情境中,沒有進貢物,百姓就獻詩朝廷,以表心跡。獻詩或進貢,代表著百姓生活的心聲,這是雙軌並行於世。所謂天下,便是透過華、夷之間的德惠而互相尊重。這是治理水土之後,接著便是處理對外關係,“貢”便是典範。透過“貢品”,人君便知道百姓在吃甚麼。有了“獻詩”,人君便理解百姓心聲。詩於是成為王官之六藝學。“獻詩”和“朝貢”是身份認同的公共行為。
結論:《大學》開出優美而充實的心靈
大學之道,由心開始,在明明德,是自己的心,這是天生的德。天生光明磊落的德是謂明德。明明德,是把明德彰顯出來。親民的是身邊的所有人。止是道德的實踐,至善是最高的道德境界,這便是“盡美盡善”。把明德彰顯於天下,天下不單指Gobal。天下還有天,Gobal只有下。孔子就是明其德於天下,匹夫而為百世師,魯國在孔子在位時曾大治三個月。齊家是順血緣關係提升生活的意義。血緣關係沒有約束力,但有感染力。齊不是整治,齊家不是抹掉人性。齊是互相尊重和諧生活的態度。互相尊重是在自身開始,所以要修身。修即“美”。美是因為正心,心安,方能有所正。心正自得其所善。世間一切真道義,都是從善意開始。這一份善意,是謂“誠”,故要誠其意。在動念之間的第一念,已經顯示對世界愛護與關懷,這是天生的良知良能,是謂先致其“知”。張開此良知,便脫離獸性,從一心而至天下,美善呈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