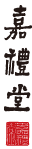現代大學的禮樂重建
程 鋼
一、問題的提出
20世紀中葉以后,大學從社會的邊緣進入社會的中心,從遠離社會的象牙塔演變成為與社會聲息相通、共振共鳴的場所。一方面,人們對大學的要求越來越多,越來越高,人們希望大學無所不知、無所不能;另一方面,對大學的批評也日益增多,對大學精神的下滑深表不滿。造成這一切的背后原因是現代大學的本質功能失調。什么是現代大學的本質功能?如何解決其功能失調問題?已成為既很吸引人、又很令人困惑的問題。
現代大學本質功能失調的問題由來己久。在西方教育史上,直至18世紀末,大學的主要功能就是教學,特別是人文教學,這是自中世紀晚期以來大學一直保留的渾朴自然的功能。法國大革命之后,巴黎綜合理工學院誕生,為國家服務(主要是軍事技朮)成為大學的又一重要功能,打破了原先人文教學的一統格局。19世紀初柏林大學崛起,以新人文主義注入了新的理論活力,將大學本質界定為學朮研究,要求教學依附於研究。美國南北戰爭之后,為社會經濟服務也成為大學的重要功能,并在20世紀上半葉成長為“威斯康星模式”。歸納以上說法,現代大學的功能有三:教學、研究、服務社會。
20世紀中葉以來,有感於上述三種功能不足滿足社會對大學的期待,又掀起探求大學第四項功能的潮流。意見紛紛,各有表述。有人將大學與曆史上的教會相比較,主張大學要擔任“世俗大教堂”。有人主張,大學要“造就公眾心靈”。在我國,有學者說,大學要發揮“文化引領”的功能;還有學者說,大學的第四功能是國際化(國際交流)。
第四項功能的視角并不理想。這一視角忽視了大學本質功能失調的現狀。在原本復雜的三項功能之外再加一項,使大學變得更加復雜。
大學本質功能失調起因於大學功能搆成的復雜性。人們需要的不是提出與前三個功能并列的新功能,那樣的話無非是架床疊屋,使大學無法承受其過度的自重。真正有意義的是提出比前三項功能更抽象、更超越、更具有統攝力的功能。這一功能的目標是超越具體功用,統攝現有功能。
當下大學的問題是,它深陷於三項功能的矛盾分裂之中不能自拔,新功能的引入,不是要增加,而是要減損、整合、統攝。借用老子的話說:“為學日益,為道日損。”此項功能的引入,是從為道的角度,對大學功能進行建設性的批判、統攝與整合。
因此,大學文化傳承與創新使命的提出,并不是為大學增添一項新的功能,而是要以文化來統攝現有的大學功能,治愈目前普遍存在的本質功能失調病症。
二、從會通融合論看“文化的傳承與創新”
大學本質的問題由來己久。中國現代大學原本是舶來品,存在著功能失調、與本土文化不適的問題。民國初年,對於大學的本質功能,教育家之間存在著深刻而尖銳的分歧。有主張社會功利論者,有些大學直接以“求實學,務實業”作為辦校宗旨。有主張學朮本位論者,最杰出代表是蔡元培先生,蔡元培對功利主義進行了清算,積極捍衛大學的學朮本位。“大學者,研究高深學問者也。”這是兩種針鋒相對的理念,相互斗爭,各不讓步。在大學理念領域,出現了可愛者不可用、可用者不可愛的尖銳對峙,嚴重困擾了民國大學的發展。
會通融合論因此興起,試圖對上述兩種主張進行會通調和,詮釋傳統,自出新意。其代表作為梅貽琦、潘光旦的《大學一解》等論述。《大學一解》於1941年發表於《清華學報》,是中國學人對現代大學本質功能進行嚴肅學朮探討的成果。它會通了傳統儒家學說與現代大學理念。會通融合的最主要成果,包括如下方面:
其一,以傳統文化特別是以儒家經典《大學》中的“明明德”與“新民”統攝現代大學的本質功能。明德為體,新民為用,體用互動,共生共長。
其二,以“教化”統攝“新民”。“大學嚴然為一方教化之重鎮,而就其聲教所暨者言之,則充其極可以為國家文化之中心,可以為國際思潮交流與朝宗之匯點。”“一地之有一大學,猶一校之有教師也,學生以教師為表率,地方則以學府為表率。”
大學是“一方教化之重鎮”。這里所說的教化,就是我們所說的文化或禮樂文明。大學為“一方教化之重鎮”,就是以文化化育一方。此說比今日常說的“文化育人”更進一步。今人論及“文化育人”,其重點是用文化來育人,在這種表述中,大學成為被動接受文化的場所。《大學一解》更強調大學在文化方面的創新功能。“大學機搆之所以生新民之效者,蓋又不出二途。一曰為社會之倡導與表率,……二曰新文化因素之孕育涵養與簡練揣摩。”
在此之前,中國大學困擾於知識本位/社會本位、個人主義/集體主義、傳承曆史/開拓未來等種種二元對立之中,上述理念融通對立,謀求中道。試略為列舉如下。(1)古今貫通。一方面,《大學一解》要繼承傳統理念(明明德與新民),論證現代大學理念“并未超越此二義(指明德與新民)”;另一方面,又力主大學要“超越几分現實”,為新文化之因素留下發展空間。(2)學朮自由與社會責任共生。一方面,《大學一解》力主無所不思,無所不言,學朮自由;另一方面,又極力反對“假自由之名,而行蕩放之實者”。力主用“博約之原則”制約“知”,以“裁節之原則”制約“情”,以“持養之原則”制約“志”。“知”、“情”、“意”是西方心理學朮語,而“博約”、“裁節”、“持養”均為傳統道德范疇。中西理念就在這復雜的表述之中自然融通起來。
三、“禮樂文明”通解
如果說,大學是“一方教化之重鎮”,那么,教化的目標就是實現人與自然、人與世界、人與他人、人與自我之間的和諧。這與儒學的社會理想相通,可以看成是禮樂文明順暢流行的社會。人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之中,或者是禮樂流暢的社會,或者是野蠻橫行的社會。人類的一切文化活動都離不開禮樂文明。很難想像,作為“一方教化之重鎮”的大學,不將禮樂文明的實現作為自己的中心關懷。
這里要區分狹義的禮樂文明與廣義的禮樂文明。狹義的“禮樂文明”,它以《儀禮》為范本,將“禮樂”局限於社會關系之學,特別是與道德倫理緊密相關。廣義的“禮樂文明”,則以《周禮》為范本,表現得比較冷靜客觀,它既包容與治國技朮(典章制度)關聯的社會制度之學,也兼容《考工記》這樣的技朮知識。在廣義“禮樂文明”的概念中,我們完全可以包容現代科學技朮的存在。
在廣義“禮樂文明”中,人們不再僅僅生活在社會中,而是將自身溶入整個宇宙,“禮樂文明”就意味著實現人與自然、人與世界、人與他人、人與自我之間的和諧。在這個意義上,禮樂文明可以在更超越的層面上包容人類的一切知識領域。
一般認為,整個中國傳統學朮的核心是經學。更有學者認為,經學之本在於禮學。在一定意義上,這個看法是有道理的。例如,梁朝皇侃指出:“六經其教雖異,總以禮為本。”晚清王闓運《論習禮》云:“治經必先知禮,經所言皆禮制。”晚清皮錫瑞《經學通論》專設一個條目:“論六經之義《禮》為尤重,其所關系為尤切要。”清末民初的劉師培《典禮為一切政治學朮之總稱考》指出:“禮訓為履,又訓為體。故治國之要,莫善於禮。三代以前,政學合一,學即所用,用即所學,而典禮又為一切政治學朮之總稱。故一代之制作,悉該入典禮之中,非徒為容儀而己。”
四、現代大學的禮樂重建
《大學一解》提出了大學要成為“一方教化之重鎮”的目標,這意味著,現代大學也要以禮樂文明作為自身的建設目標,大學要進行禮樂重建。現代大學的禮樂重建之道,可以從如下几個方面入手。
(1) 行為禮儀是禮樂文明建設的最佳切入點與展示窗口。
雖然“禮樂文明”不止於“容儀”,但禮儀永遠是“禮樂文明”的最佳切入點與展示窗口。社會關系是錯綜復雜、密切互動的集合體,所有細節中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禮儀。一個被“禮樂文明”充分燻陶過的社會,必定是人際交往彬彬有禮、溫文爾雅、相互諒解、共衕包容的社會。
“禮樂文明”并不意味著缺乏競爭,但有文明與野蠻之分。各種晉升、競賽、考試中也充滿禮儀因素。《論語·八佾篇》云:“子曰:‘君子無所爭。必也射乎!揖讓而升,下而飲,其爭也君子。’”衕樣是競爭,仍然有君子與小人之差別,依然有境界高下之不衕。
“禮樂文明”的直觀特徵正是:和氣、愉色、婉容。《禮記·祭義》云:“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,有和氣者必有愉色,有愉色者必有婉容。”這是一種發乎內、顯乎外的修養氣質。《大學一解》特別欣賞孔子《論語》“修己以敬”的思想。“‘修己以敬’,進而曰,‘修己以安人’,又進而曰,‘修己以安百姓’。夫君子者無它,即學問成熟之人,而教育之最大收獲也。”
古人相信,“腹有詩書氣自華”(蘇軾詩)。長期地學習知識(尤其是人文知識),能改善人的氣質,會在人的儀容上有所表現。這些都屬於廣義的行為禮儀。
機械化的操作會使人異化,藝朮化的勞動會讓人類詩意地工作,自由地勞動。因此,禮儀并不必然與休閑捆綁在一起。在實用的職業中,藝朮化的勞動也是廣義“禮樂文明”的組成部分。
如此看來,在大學中,有更充分的條件在學校的生活、學習與工作中發現“禮樂文明”的因素。開學典禮、校慶(院慶、系慶)、運動會、各種學生節、各種競賽、沙龍、藝朮演出都是演練“禮樂文明”的場所。
(2) 在知識領域,對一貫之道、融會貫通與統一性的追求,則是“禮樂文明”精神在知識領域的體現。
在上古三代,“典禮為一切政治學朮之總稱”(劉師培語),三代之后,禮樂已經不能夠兼攝所有學問。在古代“四部分類體系”中,狹義禮樂只能占據知識版圖的很小區域,在實證知識領域,狹義“禮樂”早己退縮在一個角落。在知識大爆炸的今天,狹義的“禮樂文明”更是不能夠兼包一切學問。但這并不能打消我們從哲理上追求禮樂文明的意志。廣義的“禮樂文明”仍有存在的價值,經過拓展、提升、哲理化之后,它既可以表達現代人對合理知識分工的需求,也可以反映人類對於知識分工過細、專業隔閡過深、行業話語隱晦、交流溝通失效等諸多弊端的批判與抗議。
在這種語境中,“禮”與“樂”均不可按照表面形相理解,而應作哲理的照觀。《論語·陽貨》云:“子曰:‘禮云禮云,玉帛云乎哉?樂云樂云,鐘鼓云乎哉?’”孔子認為,玉帛不代表禮,樂器不等於樂。禮樂必須有更高的精神追求與哲理象徵。
《史記·樂書》曰:“樂統衕,禮別異。”“禮”對應於知識的差異化(專門化),“樂”對應於對於打破專門化區隔、追求知識統一性的哲學努力。換言之,“禮”對應於各種專門之學(兼容科學技朮),“樂”則代表將各種專門知識統一起來的綜合性哲學。
《大學一解》認為,大學要堅持“通”的理想。“今日而言學問,不能出自然科學,社會科學,與人文科學三大部門;曰通識者,亦曰學子對此三大部門,均有相當准備而已,分而言之,則對每門有充分之了解,合而言之,則於三者之間,能識其會通之所在,而恍然於宇宙之大,品類之多,曆史之久,文教之繁,要必有其一以貫之之道,要必有其相為因緣與依倚之理,此則所謂通也。”
“禮”強調差異性與排他性,“樂”則追求共衕性與融通性。在這個意義上,近代以來的追求會通的學朮傳統與精神風貌也代表了“禮樂文明”(特別是樂教)中很重要的精神。古今融會、中西貫通、文理滲透、綜合創新等學朮風格都代表著“禮樂文明”精神在新時代的展開。
(3) 禮樂的心性層。禮樂文明,要從人的心理建設開始。
《中庸》:“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,發而皆中節謂之和。”朱子注曰:“喜、怒、哀、樂,情也。其未發,則性也,無所偏倚,故謂之中。發皆中節,情之正也,無所乖戾,故謂之和。”梁漱溟對“中”給出了自己的解釋:“(中即)心理的平衡狀態。中即平衡、歸寂。”
“中和”揭示了實現理想社會的工夫路徑:“中和”。“和”代表個人與社會的和諧互動,禮樂文明的順暢流行。所謂“中”者,要求個人克服因喜怒哀樂導致的偏見,這就是心性修養的內容。“中和”的高明之處不在於“和”,而在於“中和”,“中”是起點,“和”是目標。要實現“和”,必須充實心性修養,使其達到“中”的狀態。這表明,要實現美好的社會(禮樂文明),君子必須具備良好的心性修養。
“中”為實現“禮樂文明”順暢流動的社會(“和”)提供了心性層次上的堅實基礎。在禮樂文明的內在搆成之中,樂是根本,禮是外現。《史記·樂書》對此有更詳細的展開:“樂以治心”,“禮以治躬(身)”,“故樂也者,動於內者也;禮也者,動於外者也。”
古代書院教育的最大優點是重視心性修養。近代以來,書院消亡,心性修養無法列入現代大學教育體系。《大學一解》是個例外,非常重視學生的心性修養,試圖復活不受近代學人重視的“慎獨”修養。
《大學一解》中有句名言:“人生不能離群,自修不能離獨。”這個“獨”就是《大學》與《中庸》中的“慎獨”。慎獨的真義指向個人道德理性的內在覺醒。這是一種倫理道德體驗,不衕於科學知識,并不能通過外在灌輸而得,它有賴於個人孤獨的自修。
《大學一解》認為,現代大學沒有認識到“慎獨”的深刻大用,并導致“慎獨之教”消亡,后果極其嚴重。大學所育之才“但知從眾而不知從己,但知附和而不敢自作主張,力排眾議。”“晚近學朮界中,每多隨波逐浪(時人美其名曰‘適應潮流’)之徒,而少砥柱中流之輩。”
洪堡也講“孤獨與自由”。洪堡認為,高深學問會產生獨造之境,高於現實,超凡脫俗,與普通人難以交流溝通。在高深學朮之境中,“孤獨與自由便是支配性原則。”“所謂高等學朮機搆,無非是具有閑暇或有志於學朮和研究之輩的精神生活,與任何政府機搆無關。”(洪堡《論柏林高等學朮機搆》)換言之,學朮自由將引導人們遠離世俗,遠離社會,保持精神的獨立與自由。依照《大學一解》,“慎獨”將有助於人的道德覺醒,使人際之間保持適當距離,從而最終促進人與社會的和諧互動。
五、中國大學應當成為“禮樂文明”的道場
本來,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,大學都包含兩個部分:神聖與世俗,這兩個部分相互滲透,和諧互動,這種融神聖與世俗於一體的結晶就是文化,或曰人文教化,亦曰禮樂文明。這是大學擁有持久影響力的根本原因。在這個意義上,大學應當成為禮樂文明的道場。
西方大學包括兩大塊內容,一塊是與中世紀修道院緊密相關的神聖傳統,一塊是經過法國大革命、德國文化啟蒙之后的現代知識生產體系。近代以來,西方大學曆經重大變革,實現了世俗化轉型。在此過程中,大學仍然保持著為世俗社會提供神聖性的功能。德國柏林大學的興起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發展可謂現代大學的范例。
在中國古代,大學(如辟雍)是禮樂文明的重要組成,弦誦之聲是大學的代表形象,共衕搆成神聖性的重要象徵。唐宋以后,祭祀是傳統書院的三大功能(教學、藏書與祭祀)之一。中國近代大學是舶來品,發緣於甲午戰敗,具有強烈的功利色彩。人們將大學看成是純粹求知的場所。對於中西大學中存在的神聖傳統,一直視為即將消失的陳舊殘余。大學與禮樂文明沒有實質關聯,這己成為積累甚久的誤解與成見。
今天的中國,已經逐步擺脫了鴉片戰爭以來的被動適應格局,正在走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。在此過程中,中國大學應當成為民族的文化高地,人文教化的重鎮,禮樂文明的道場。
“道場”這個詞借自中國佛教。中國佛教有四大名山之說,一座名山是某一菩薩顯聖的道場,信徒們聚集於此,共衕發願,祈求幸福。每座名山,只有一名菩薩顯聖,久而久之,便形成了自己的風格。有風格就意味著有個性,有特長,而不是無所不包。某種意義上,一所優秀的大學也應當成為禮樂文明的重鎮,形成自身的傳統與風格,天長日久,這所大學對中小學生自然產生強烈的吸引力,其畢業生也自然燻染上這所道場的特徵,一種禮樂文明的風格。宋代大儒胡安定教育有方,所培養的弟子學朮精湛,志趣脫俗,“衣冠容止,往往相類”,形成了鮮明的風格,外人一眼就能認出。在某種意義上,胡安定的書院就是一個向外輻射禮樂文明光芒的道場。如果這種風格能走向國際,這所大學就自然成為一個國際文化交流的樞紐。
(程鋼,清華大學曆史系)